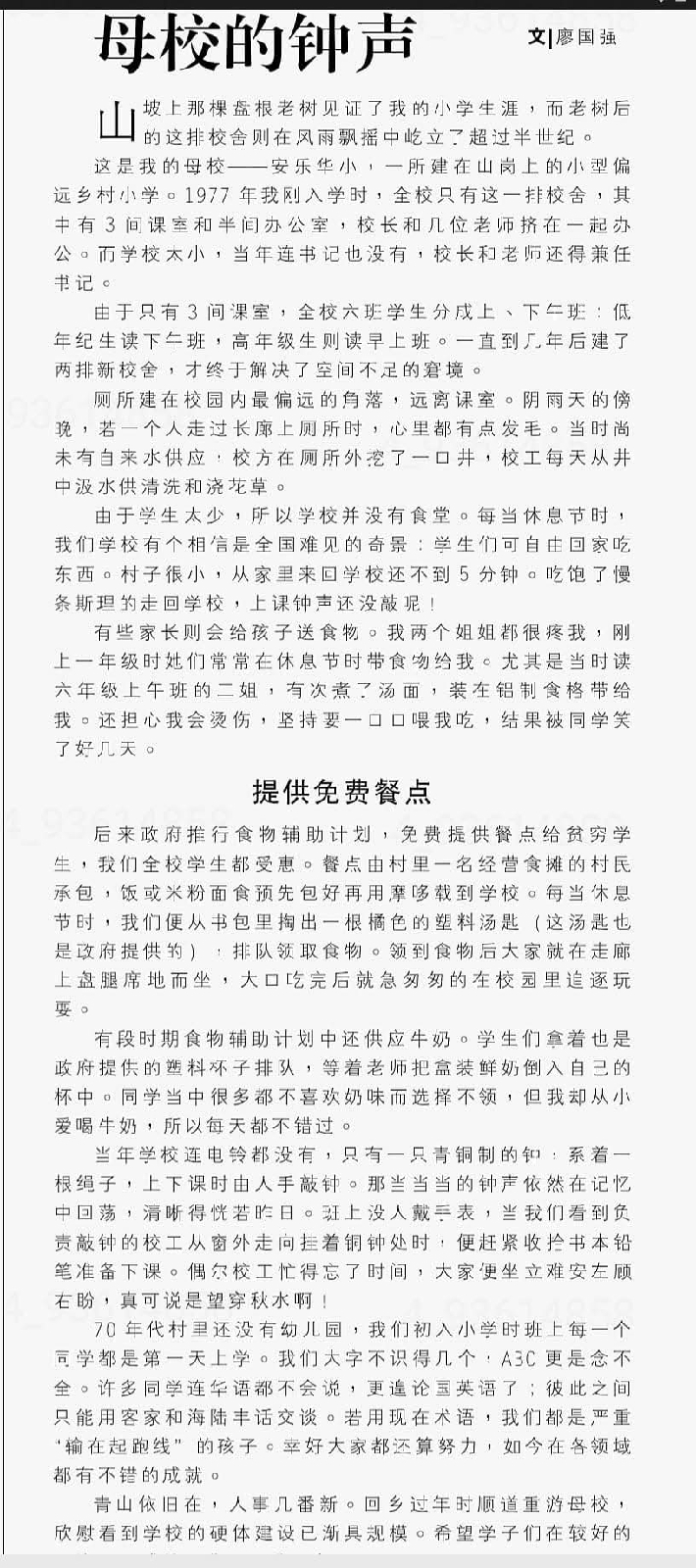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以〈迫在眉睫的糧食災難〉"The coming food catastrophe" 為主題,刊登了好幾篇關於糧食危機的專題報導。
世界各國所生產的糧食原本足夠餵飽全球人口,然而最近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卻讓糧食供求失衡,尤其是小麥和食用油,進而引發了迫在眉睫的危機。
首先是氣候變遷,從去年起長時間的乾旱和過於炎熱的天氣,使到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世界最大的小麥生產國歉收。印度為了穩定國內的需求,也在五月中宣布禁止小麥出口。
而造成糧食供應不足的更直接導因則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的戰爭。俄烏兩國是世界葵花籽及小麥、大麥、玉米等穀物,以及農業化肥原料的重要出口國。小麥佔了28%,而葵花籽油更是佔了全球75%的市場。戰爭讓這些糧食無法出口,嚴重影響全球糧食供應。
本期《經濟學人雜誌》的系列文章中指出,原本烏克蘭生產的穀物和食用油是通過Odessa港口、經黑海運往海外。但俄烏戰爭爆發後,俄羅斯軍事封鎖了這海域。而烏克蘭為了防止俄軍攻占這重要海港,則在海面設置了大量水雷,使得該國唯一的海運出口無法通航。
由於無法出口,烏克蘭農民已收割的小麥大量囤積在倉庫裡日漸腐爛,外面的世界卻因為小麥的短缺而價格狂飆。小麥期貨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漲了40%,嚴重影響了以小麥為主食的人民,尤其是非洲一些較貧窮國家。
而葵花籽油的短缺令部分市場轉向棕油,使得棕油期貨價格狂漲。最大生產國印尼的棕油產量雖佔了全球總產量超過五成,但高漲的棕油價讓業者把絕大部分棕油出口,使得國內市場貨源短缺。為了安撫民怨,印尼政府也在五月間禁止棕油出口,進一步加劇全球糧食危機。
一旦全球短缺,大部分的糧食肯定將優先供應給出得起高價購糧的國家。這情況在去年初Covid疫苗供不應求時期已出現過了。
除非俄烏早日恢復和平,否則糧食供需失衡的問題勢必將使得各國生活成本繼續惡化,並極可能演化成一場人道危機。